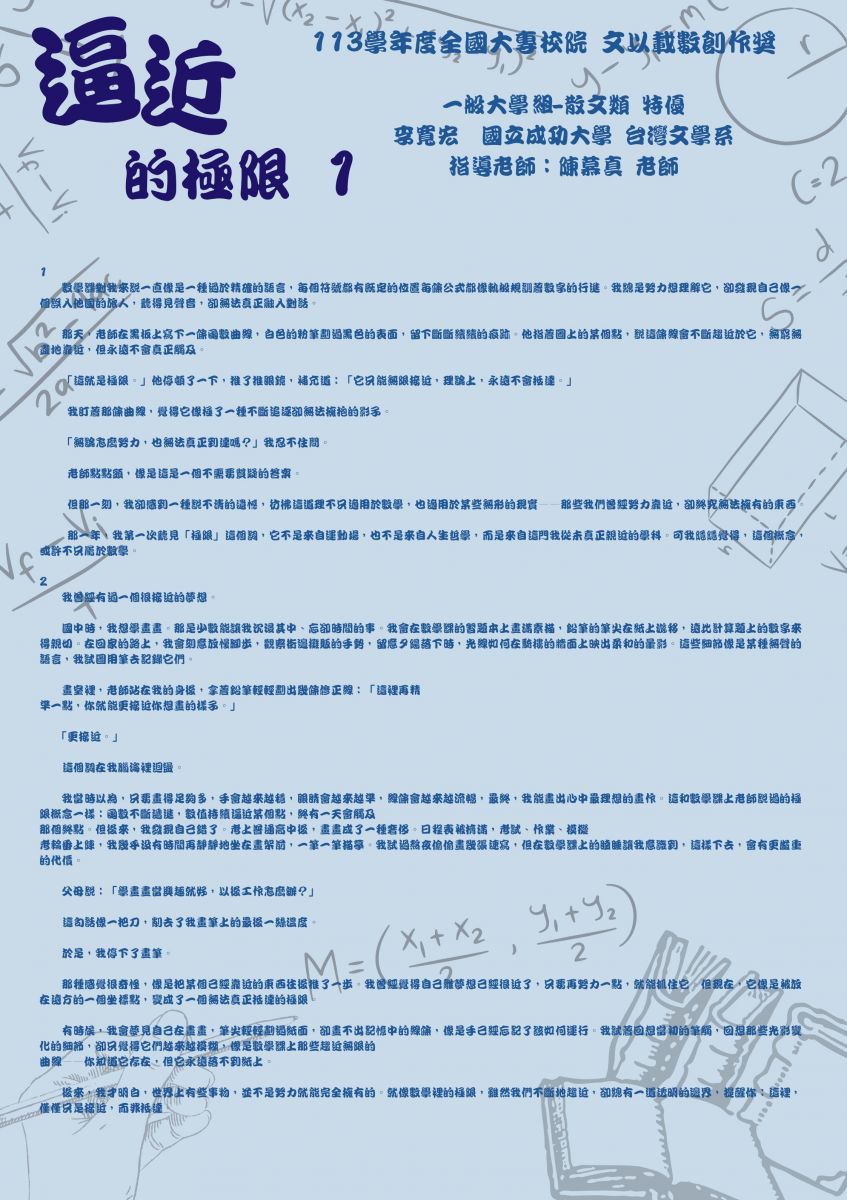

1
數學課對我來說一直像是一種過於精確的語言,每個符號都有既定的位置每條公式都像軌般規訓著數字的行進。我總是努力想理解它,卻發現自己像一個誤入他國的旅人,聽得見聲音,卻無法真正融入對話。
那天,老師在黑板上寫下一條函數曲線,白色的粉筆劃過黑色的表面,留下斷斷續續的痕跡。他指著圖上的某個點,說這條線會不斷趨近於它,無窮無盡地靠近,但永遠不會真正觸及。
「這就是極限。」他停頓了一下,推了推眼鏡,補充道:「它只能無限接近,理論上,永遠不會抵達。」
我盯著那條曲線,覺得它像極了一種不斷追逐卻無法擁抱的影子。
「無論怎麼努力,也無法真正到達嗎?」我忍不住問。
老師點點頭,像是這是一個不需要質疑的答案。
但那一刻,我卻感到一種說不清的遺憾,彷彿這道理不只適用於數學,也適用於某些無形的現實——那些我們曾經努力靠近,卻終究無法擁有的東西。
那一年,我第一次聽見「極限」這個詞,它不是來自運動場,也不是來自人生哲學,而是來自這門我從未真正親近的學科。可我隱隱覺得,這個概念,或許不只屬於數學。
2
我曾經有過一個很接近的夢想。
國中時,我想學畫畫。那是少數能讓我沉浸其中、忘卻時間的事。我會在數學課的習題本上畫滿素描,鉛筆的筆尖在紙上游移,遠比計算題上的數字來得親切。在回家的路上,我會刻意放慢腳步,觀察街邊攤販的手勢,留意夕陽落下時,光線如何在騎樓的牆面上映出柔和的暈影。這些細節像是某種無聲的語言,我試圖用筆去記錄它們。
畫室裡,老師站在我的身後,拿著鉛筆輕輕劃出幾條修正線:「這裡再精
準一點,你就能更接近你想畫的樣子。」
「更接近。」
這個詞在我腦海裡迴盪。
我當時以為,只要畫得足夠多,手會越來越穩,眼睛會越來越準,線條會越來越流暢,最終,我能畫出心中最理想的畫作。這和數學課上老師說過的極限概念一樣:函數不斷遞進,數值持續逼近某個點,終有一天會觸及
那個終點。但後來,我發現自己錯了。考上普通高中後,畫畫成了一種奢侈。日程表被擠滿,考試、作業、模擬
考輪番上陣,我幾乎沒有時間再靜靜地坐在畫架前,一筆一筆描摹。我試過熬夜偷偷畫幾張速寫,但在數學課上的瞌睡讓我意識到,這樣下去,會有更嚴重的代價。
父母說:「學畫畫當興趣就好,以後工作怎麼辦?」
這句話像一把刀,削去了我畫筆上的最後一絲溫度。
於是,我停下了畫筆。
那種感覺很奇怪,像是把某個已經靠近的東西往後推了一步。我曾經覺得自己離夢想已經很近了,只要再努力一點,就能抓住它。但現在,它像是被放在遠方的一個坐標點,變成了一個無法真正抵達的極限。
有時候,我會夢見自己在畫畫,筆尖輕輕劃過紙面,卻畫不出記憶中的線條,像是手已經忘記了該如何運行。我試著回想當初的筆觸,回想那些光影變化的細節,卻只覺得它們越來越模糊,像是數學課上那些趨近無限的
曲線——你知道它存在,但它永遠落不到紙上。
後來,我才明白,世界上有些事物,並不是努力就能完全擁有的。就像數學裡的極限,雖然我們不斷地趨近,卻總有一道透明的邊界,提醒你:這裡,僅僅只是接近,而非抵達。
3
考大學那年,我的數學成績依舊普通,勉強夠用,卻沒有讓人驚豔的亮點。我沒有.選擇和數學相關的科系,甚至有些刻意地避開它,像是對一個曾經讓自己挫敗的事物產生了條件反射。我心想,這樣或許能讓自己遠離那些枯燥的方程式、不再與極限為伍,彷彿只要轉身,就能甩開過去那些總是算不對的數值、永遠達不到的終點。
但數學,從來不是一件能輕易放過你的事。
大學的第一堂通識課,教授站在講台上,寫下了一串熟悉的符號,白色粉筆在黑板上劃開一道清晰的痕跡。我原本正低頭看課表,聽見「極限」這個詞時,手上的筆微微一頓,心底浮起一種異樣的熟悉感。
「極限,」教授輕輕敲了敲黑板,「不代表你無法到達,而是它指引你該前進的方向。如果你不去計算,你永遠不會知道它到底會趨近於哪裡。」
他停頓了一下,轉過身來,似乎想給我們時間思考這句話的意義。我低頭望著課桌上自己隨手畫的鉛筆線條,那些線細細密密地交錯,有的起點模糊,有的乾脆沒有終點。這些圖像像是某種隱喻,提醒著我,那些未竟的事情,那些尚未落筆的選擇。
那一瞬間,我忽然明白了很多事情。
或許,畫畫這件事並沒有真正結束,只是被我擱置在一條不同的數線上。我以為自己選擇了遠離,卻沒發現,某些軌跡依舊隱藏在生活裡,等待著某一天與我再次相交。
或者,那些關於人的距離,也是如此。
4
我開始重新畫畫,不是為了考試,也不是為了證明什麼,而是因為我終於明白,無論我曾如何偏離、如何停滯,這條路依舊存在,就像數線上的某個點,等待著被再次標記。它從未真正消失,只是被我遺落在過去的某個象限裡。
我不再試圖用尺規畫出完美的直線,也不強迫自己臨摹那些標準的人物比例。我開始隨性地落筆,任由線條穿梭在紙面上,像是不受控制的方程式,有時收斂,有時發散,卻都帶著自己的節奏。我想,數學和畫畫或許並沒有太大差別,本質上,它們都是一種尋找——尋找世界的規律,也尋找自己。
有一天,我在書店翻閱一本畫冊時,遇見一個神色苦惱的學弟。他的手裡拿著一本數學參考書,書頁上滿是密密麻麻的計算痕跡,像是試圖將某個難解的問題逼到極限,卻仍舊找不到出口。他抬頭看見我,嘆了口氣:「學長,你數學好嗎?」
我愣了一下,然後笑了:「不好,但我後來換了個方式去理解它。」
他皺起眉,像是不明白我的意思。我指著書上某條趨近某個數值的函數,問他:「你覺得這條線,為什麼要不斷逼近某個點?」
他盯著那些曲線,低聲說:「因為它的目標是到達那裡。」
「可是它永遠不會真的抵達。」我輕輕合上書本,說:「你覺得這樣,還有意義嗎?」
他沉默了一會兒,然後搖搖頭:「如果永遠無法到達,那不是很挫折嗎?」
我看著窗外,夕陽斜照進來,光線落在地面上,長長的影子與貨架交錯,像是一條錯綜複雜的數線。我忽然想起高中的數學課,想起那時候的我,坐在最後一排,問老師這個問題:「無論怎麼努力,也無法真正抵達嗎?」
我曾經以為,這是一種缺憾,一種無法跨越的障礙。但現在,我卻有了不同的答案。
「極限不是一道你無法翻越的牆,它是一條指引你前進的路。」我慢慢地說:「我們努力的每一步,都是為了讓它更靠近,哪怕永遠不會抵達,但這並不意味著沒有價值。因為在那趨近的過程裡,我們已經改變了自己。」
他靜靜地看著我,似乎在思考這句話的意思。
「就像畫畫一樣。」我笑了笑,拿起一旁的畫冊翻開,「我們永遠畫不出一張完美的畫,但我們可以不斷修正、不斷精進,讓它更接近我們想要的樣子。」
陽光漸漸變淡,時間推移,窗外的影子拉長又縮短。書店裡播放著低聲的音樂,數學參考書的紙頁微微翹起,像是被歲月翻閱過的記憶。
學弟點了點頭,輕輕地說:「好像有點懂了。」
他抱著書走向結帳櫃檯,而我站在原地,翻開畫冊,目光落在某個未完成的素描上。筆觸停留在紙上,像是某個正在趨近的函數,等待著下一筆落下,等待著它的極限。
或許,真正重要的,從來不是抵達,而是我們如何走向它。
 文以載數創作獎
文以載數創作獎